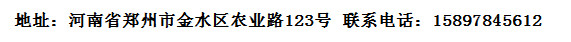我对生命的思索
白癜风早期 http://www.bflvye.com/天涯信笔/文现在医学发达了,人的寿命也在延长。现在常听说有人活到一百岁,有人活到了一百零几岁,不免心生羡慕。其实,这些人未必值得羡慕。人们往往只看见他们的寿数,没看见他们的无奈。这些寿星老人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中,很可能有十年在忍受着糖尿病和关节炎的折磨,另外十年与拐杖和轮椅相伴,最后十年偏瘫在床或处于痴呆中。人生最美好的时期是六十岁以前。六十岁尤其是七十岁以后生命的价值便开始衰减。这种衰减,一方面体现在生活的乐趣越来越少,因疾病或者味蕾的退化不能享受美食,因为体力的衰退不能畅游世界;另一方面体现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生理上的痛苦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人在到达生命终点前还不得不熬过一个苦难期。这个苦难期往往与长寿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这个时期苦多乐少,大多数人还是留恋生命,紧紧抓住这只有一次的生命的尾巴。我少年时代对死亡非常恐惧。我对死最青涩的理解是灵魂突然坠落到黑暗的深渊中,那里寒冷而孤独,而且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将不得而知,而且永远绝缘。老年后,眼看着熟人一个个离去,也目睹着亲友在死亡线上挣扎,痛惜之中逐渐修正着我的生死观。我的岳母已经90多岁了。多年来她一直与房颤等多种疾病做斗争。最近几年,她因骨质疏松,脊椎多次压缩性骨折,因此对她既不能背又不能抱。她多个脏器衰竭,胸部积水,极易感冒。医院看病都必须出动三人:一人开车(医院周边难以停车须把车先开回家),一人推轮椅兼贴身照顾,一人跑科室联系医生和缴费。她生活的乐趣是读报看电视。她活着的唯一医院的岳父还需要她。我下面要提到的岳父是另一个生命价值衰减的长寿例子。我直面的第一桩死亡是父亲的离世。文革结束前夕,父亲罹患肝癌。在医院确诊的两个月后父亲离去。肝癌一般是很疼痛的。医院里见过在疼痛中哀嚎的肝癌病人。父亲很担心会出现这一幕,自己受苦,也让亲人心如刀绞。父亲担心的事最终没有出现。他在生命的最后24小时里一直在打嗝而一刻不能入眠。这虽然使他很难受,但却没感到需要哀嚎的地步。他觉得维护自己最后的形象很重要,因为这是一种尊严。六年后母亲也走了。她是在公园游园时突发脑溢血倒地,医院八个小时后离世的。当时我处于研究生毕业前夕。晚上八点接到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曰:“你母病危,望速归。”这是父亲的同事和好友发来的。晚上十点,邮递员敲开学校的大门送来第二封加急电报:“你母已故,速归。”这两封电报都是父亲的同事发来的。第二天我登上火车回家奔丧。亲朋故友中的老人见了我第一句话是“人死不能复生,望节哀顺变”,然后无一例外的加上一句“你妈好福气,自己没受罪也没让子女受罪,前世积的德呀!”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由衷地羡慕。这句令我不大受用的话,我多年之后才深深地体会到是一句出自肺腑的真心话。记得母亲曾说过,她最怕的疾病是偏瘫。她倒地后没有再醒过来,这遂了她的愿。而在当时我们心中总有“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遗憾。七年前,我的岳父突患脑梗失去知觉,一个星期后才醒过来。从此半身不遂,失去说话、进食和翻身的能力。营养靠鼻饲供给,小便靠导尿管,大便靠尿片。为了防止褥疮,护工每两小时替他翻一次身,并且定时按摩。他最痛苦的是吸痰。由于不能坐起和缺乏活动,肺部积痰增多,而他没有主动咳痰的功能,只能靠护工从咽喉插入一根塑料管,用气泵将痰抽出。插吸痰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他每次都非常抗拒。这个过程一天要经历二十多次。他睁开眼的时候面无表情。我们为了测试他是否有意识,把报纸反着递到他还能勉强动的左手里。他看看报纸,慢慢地将报纸转了一百八十度。他的意识非常短暂和微弱。问他任何话,他只会摇头,不会点头。我猜想他的点头功能已经丧失。他有时候是想点头,但做出来的动作却变成了摇头。他经常向亲人露出哀求的目光,那目光是恳求亲人放弃对他的治疗。亲人们装着看不懂,继续说着宽慰他的话。于是,在吸痰时他便紧紧咬着吸痰管不让插,但在亲人们耐心地劝说下,他又缓缓张开嘴。最难堪的是,他不得不在亲人的面前赤身裸体地接受护工翻过来翻过去地摆弄,下体还插着尿管。女儿和儿媳们对此已见惯不怪,丝毫没有觉得有回避的必要。这一幕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我从此意识到:死亡不可怕,世界上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没有质量和没有尊严的活着。我们的同事W君在离世前就在这种状况中煎熬了几年。我经常思考长寿的意义。长寿并非都是痛苦和没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病痛是可控的;第二条件是生命是有尊严的;第三个条件是有亲情和关怀。我的邻居是一个96岁的老人,虽然做了三次癌症手术,但恢复得很好,现在在附近的小公园里经常看到他散步的身影。他的生活起居由一位保姆照料。六个女儿轮流来看望他,陪他过周末过节。然而,我的街坊中更多的是相反的例子。我家的楼上有一位独居的老太太。老伴过世后靠微薄的遗属津贴和老伴的存款生活,身体多病基本无法无法自理,每天只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去吃食堂又油又咸的饭菜。有一天她在电梯里激动地对大家说:“我儿子明天要来带我去看病,”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她身体每况愈下,连楼都下不了了,食堂只能每天派人把饭菜送到她家。还有一对失能的老夫妇,三个女儿中一个在外地,两个在国外。女儿们雇了一个保姆照管两老的饮食起居。后来老爹去世了。女儿们回来办完老爷子的后事后,继续让保姆留下来照顾老太太,但要把她的工资减掉几百元,原因是她的工作量减少了。保姆一气之下辞工走人。女儿们一劳永逸地把老太太送进养老院。老太太在养老院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回家。女儿们感到没有必要为这事再齐聚一次,便一直拖了下来。此事令邻居们唏嘘不已。父亲最后最后的话令我深省。父亲弥留之际对病榻前的子女们说:“别难过了,爸爸活一百岁也不能陪你们一辈子。人总是要死的,人要都不死,子子孙孙住哪里去啊?”父亲用自然规律来宽慰我们。用今天的科普语言解读就是:如果人类只生而不死,生态系统就会失衡。据估计,公元前年时世界人口为万,公元前年时世界人口为1.0亿。公元前年正好是孔子出生的时代。仅从孔子算到今天,人类就已经繁衍了70多代。如果从古至今的人类只生不死的话,今天世界应该有数千亿人口了。我们的脚下将无立锥之地。不仅是生存空间的危机,如果人类只生不死,大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也会阻断。人体重量中80%是水分。这说明构成人体的大部分物质是氢元素和氧元素。人体的其余部分主要是蛋白质和骨骼,其化学成分是氢、氧、氮、碳、钙、磷、钾、镁等。人通过呼吸和食物链摄取大自然中的这些物质。人离开这个世界后,构成人的肉体的各种元素又将返回大自然中。人来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谁也不会例外,区别无非是早一天和晚一天而已。人离开人世后化成一缕青烟回到大气中,剩下的一撮灰(主要是钙等矿物质)本来也应该回到土壤中,但却被装在盒子埋在土里。这实际上阻碍构成骨灰的物质返回大自然,也阻碍了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多年来,我们每年清明都要到父母墓地的城市为父母亲扫墓。扫墓只是一个仪式,寄托我们对父母亲的怀念,更现实的意义是为分布在各地的兄弟姐妹们提供了一个一年一次的团聚机会。姐姐和姐夫已经在父母的墓园里为自己买好了墓地。他们希望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将来为他们扫墓时顺便在我们的父母墓前也燃上一把香火。我不禁想,若干若干年后他们的子孙以及子孙的子孙还能恪守这个传统,像他们的子女一样照拂曾祖、高祖、高高祖的墓地吗?最大的可能是,未来某一年这些坟墓被当作无主欠费坟茔被移出墓园。即便我们的后人能够世世代代照拂我们的墓园,我们又何必要让子孙后代背上这个沉重的负担呢?我决定,在我故去后我的骨灰将埋在某棵树下,或洒在海里或者江河里,让它尽早回归大自然,永远免除子孙后代的负担。悼念留在心中,无需图腾膜拜。我的右耳后面有一个疣子。它非常影响理发师傅的工作。不止一医院里做一个激光手术把它除掉。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它是一个胎记。幼年时我母亲经常抚摸这个疣子。我两岁的时候曾经被一个女疯子抱走过。可能因为这个经历,母亲对我后脑勺的这个疣子特别留意,仿佛怕我再次走丢。现在每当有人建议我摘除这个疣子时,我就想起母亲。没有这个疣子,将来到了那个世界母亲还能认出我来吗?这个想法只是我对母亲怀念之情的一种心理折射。事实上,这个世界根本不分什么阳界阴间,没有灵魂也不分今生和来世。世界是物质的,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思维是人的大脑的一种功能。思维功能并不是超自然的灵魂。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不会有另一个世界等着你,也不会转世再回到这个世界,所以不用思前想后,唯一该做的就是坦坦荡荡地回到大自然中。肾结石是我老毛病了,每年的查体都说我左右肾都有石头。新冠流行的这一年石头终于掉出來了,卡在输尿管里。这是过去四十年来的第三次了。医院彩超表明这次卡在输尿管里的石头长1.0厘米粗0.7厘米(不是说好了大于0.6厘米的石头掉不出来的吗?)由于石头太大,它完成从肾脏到膀胱的行程可能要超过一个星期。医生说如果忍受不了痛苦可以约冲击波碎石手术,但做碎石手术之前要拍CT片子以确定石头的准确位置。由于病人太多,CT室把我的手术排在三个星期以后。肾结石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输尿管很细,在石头撑挤下会引起剧烈肾痉挛和胃痉挛。这两种痉挛导致浑身哆嗦甚至满床打滚,并伴随着恶心。这种发作在两到四个小时后减缓,这是因为这一段输尿管开始适应了这种挤压。但是,当石头向下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时就又会发作一次。这种痛苦每天要经历两三次。输尿管被划破后会产生炎症,因此疼痛之后又伴随着发烧。到了第五天又出现新的情况。我的左膝盖开始剧烈疼痛起来,不能打弯。自己不能穿脱裤子和袜子。妻仔细查阅了我服用的药,发现是治疗尿路感染的左氧氟沙星惹的祸。这种药的副作用中有一项是可能引起“膝盖痛,肌腱炎和肌腱断裂”。这种负作用的发生率只有万分之几,不巧让我赶上了。在肾脏痉挛、胃痉挛和肌腱炎的夹击下,真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紧接着的次日凌晨,我的鼻子突然流血不止。只能叫了一辆,到医院挂急诊。这又是我的另一个老毛病。年轻时就有干燥性鼻炎,最后导致鼻粘膜溃疡,伤及鼻子内的一根血管。医院根治一下,但又一次次拖着没有去。这次各种病都来了,医院。随着年龄的增大,由各种沉疴引起的健康危机会越来越频繁。这预示着我正在步入生命末端的苦难期。有时候想想,既然早晚要走,不如早走早解脱。三年前,二十多年的同事和好友X君罹患胰腺癌去世。去世前留下遗嘱:不举行告别仪式。医院送他。他被从太平间拉出来后直接送到火葬场。我问他妻子能不能把运尸袋的拉链拉开一点,让我看他最后一眼。他妻子哭着使劲摇摇头。经过化疗的折磨他的面容形如骷髅,而且他又捐了眼球,脸上只剩下两个空眼眶。他拒绝告别仪式,是要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当我离世时,我也谢绝追悼会。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宜接受大家的鞠躬。再者,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追悼会就像是一个无法回馈的礼品,我接受这个礼品却没有回赠的机会。最近得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了77.3岁。我还没达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标准,但想想鲁迅先生才活了55岁,诗歌天才普希金只活了33岁,另一位俄罗斯文学天才莱蒙托夫仅仅活了26岁,不久前翼装女孩刘安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降落伞意外地没有张开,她直接摔在天门山下,生命定格在26岁,我比他们好太多了。我年轻时也与死神两次擦肩而过。那是在右江河谷插队时到山区修水库。一天晚上取土场塌方,四名农村青年被埋在土下。被刨出来时三名负重伤,一人死亡。我是十分钟前正站在塌方点取土。如果我晚十分钟走开,我便是埋在下面的人中之一。另一次发生在另一个水库工地。因为大雨冲垮了临时的木桥,运送物资的卡车无法到达工地,我被派去把一批绳索挑回来。我们先涉水过河,挑上绳索再涉水回来。没想到回程我误入了深水区,我与绳索一起漂浮起来,被急流冲到断桥的涵洞里。我迅速抱住了桥面,但身体被吸入涵洞里。我如果扎一个猛子也许能从涵洞的另一头游出来。我脑子飞速地转动,评估着涵洞里的风险。上游冲下来许多树干和树枝卡在涵洞里,而我刚刚挑在肩上的绳索已经被卷进洞里了,现在恐怕正挂在树枝上,形成了一张网。我要是被冲进涵洞很可能变成缠在蛛网上的蚊子或渔网上的小虾……。我的手指死死扣着桥面坚硬的泥土,坚持了十分钟,直到赶来的同伴把我从水里拉出。我的生命才没有停留在20多岁的年纪上。那个年纪真好,心中还有滿滿的求生欲。我与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一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我当过代课老师、农民、工人、施工员,后来上过大学、读过研,然后又当老师,再后来从事研究工作。少年时代我对自己的人生有过许多设想。我的理想清单上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科学家和作家。我这一生与天文学和核物理失之交臂,阴差阳错地拐到社会科学这条跑道上来了。不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员应该算是社会科学家。这么一推理,我当科学家的梦算是圆了。退休后我回归文学爱好,把一肚子与文学有关的积累转化为铅印的文字,被北京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我的作家梦也实现了。我的一生虽平凡,但没有虚度。人的“一生”是由生命的整个过程以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组成的。完美的一生不一定要太绵长,但首先要幸福。幸福意味着你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遭,意味着在你活着的时候有人关爱你,身边也有你所关爱的人;其次,在你迈过生命的终点时要走得平平和和,最好没有痛苦并保持着尊严。.6.7.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